事企脱钩,有机遇也有险滩
- 来源:农财宝典种业版
- 关键字:事企脱钩,改革,种业
- 发布时间:2015-10-14 1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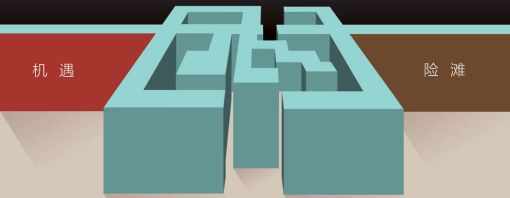
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共涉及32项改革举措、143项政策措施。距离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的科技体制改革已30年,表明改革是持续进行的,并非一蹴而就。
其中,始于1999年的院所转制,因涉及数百家科研机构从事业单位到企业的身份蜕变,意味着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对于种业来说,形成了众多科研院所、高校创办的种子企业,但是很多单位属性不清,科研与经营不分家。
30年后的今天,改革进入最后攻坚时期,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对症下药,啃掉最后的“硬骨头”。5月15日,农业部办公厅下放关于加快推进种业“事企脱钩”工作的通知,对规定脱钩的种业事业单位做出最后通牒,2015年年底必须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实现脱钩。
在国家新一轮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种业事企脱钩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到底何去何从,我们更充满期待。
必须改:符合商业化育种的需要
目前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多、乱、散、小”是我国种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品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我国90%以上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据了解,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只有2%-3%,而跨国公司一般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10%左右。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认为,长期以来,科研单位是国内种子研发项目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科研单位拿着国家的经费,掌握着核心育种资源,参与商业化竞争的“双重利益”怪圈,制约着我国种业的发展。
商业化育种需要从国家层面处理好公益性研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认为,一个强国,不可能只靠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这种作坊式的方式去做育种,而不去扶持自己的种子产业。
解决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在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按照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专家的看法,就是要突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保护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合法权益,促进产学研结合。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号)的要求,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鼓励种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股份制研发机构;鼓励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同时,要求确定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2015年底前实现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脱钩;其他科研院所逐步实行企业化改革。
但近两年来,进展似乎并不是很大。中国种子协会秘书长李立秋说,尽管各地按照国务院要求,积极研究并务实推进脱钩工作,但进度很不一致。农业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快推进种业“事企脱钩”工作的通知》,是进一步督促,确保2015年底前完成种业事企脱钩。
据农业部2004年资料显示,全国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兴办科研型实体463家,其中经营种子种苗为主体的企业123家。现在有多少家事企面临脱钩?“这个说不准”李立秋说。不过有种业专业人士估计仍在100家左右,并且主要集中在省级农科院的下属种子企业。例如,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数据统计,浙江省目前约有10%的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存在着“母子”关系,属于事企脱钩范围内的。
带来商机:引来社会资本进种业
种业这股事企脱钩热潮,无疑是对企业的发展存在极大利好。长江证券分析师陈佳认为,种业“事企脱钩”后,具备国资背景的种子公司,在资金实力、研发能力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均拥有较大的平台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加速,在此背景下,央企平台的上市种企更具资源整合、股权优化和外延发展等改革优势,能够与优质科研人才和科研资源进行更加多样化和全面的合作。
据了解,农发种业、隆平高科作为国有企业,随着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在未来资源整合和外延发展方面被多家证券公司所看好。

而哪些脱钩的事企更容易被社会资本所吸引呢?答案是有科研实力的事企。例如,鲜美种苗以总价3997.5万元收购广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将其持有的广东金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广东金作”)65%的股权;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以1259万元竞拍拿下浙江省农科院将其下属浙江农科种业有限公司36%的国有股权。
鲜美种苗总经理罗哲喜说,收购广东金作后,弥补了公司在育种研发方面的不足;而公司的投资方为中科招商,他们不但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财务管理、经营管理等先进理念。
事企脱钩后,对于一些缺乏优秀育种人才的企业来说,同样带来巨大商机。据了解,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乐公司”)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深度合作,将该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整体、小麦中心育种部分(丰优育种室)并入秋乐公司,开展商业化育种。对于研发的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开发收益按比例分配。而对于进入公司的科技人员,则按“双轨制”对待,即仅保留其事业编制,与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薪酬、福利及奖金由公司按企业薪酬体系发放。
遭遇险滩:人才流失造成企业空壳
事企脱钩的核心是育种团队的归属,有些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以能办种子企业,关键是有一个育种团队,而且这个团队能不断地育出新品种。
在事企脱钩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职工、特别是育种科研人员的权益,就会遭遇因人才流失的尴尬,企业就变成了一个空壳,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大种业兼并中小种业、投资公司或基金入股种子企业,主要看什么?李立秋认为,一是核心竞争力,就是育种创新能力;二是市场开发能力,即品牌效应。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办的种业,多数只在第一点上有优势。
有的事企尽管已经实现了改制,但后续遗留的问题仍有不少困惑。广东金作总经理刘国华说,股权改制后,公司与广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固定资产的产权问题、人员的去留问题等都需要慢慢去协商、落实。
知名种业人士林默染认为,农业科研院所攒点家底不容易,很怕“种业事企脱钩”后,上级主管部门将自己的家底直接划走或者稀释股份,控制权旁落,对“脱钩”就存在严重的抵制情绪。
当然,“种业事企脱钩”完成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那些身兼多职的种企高管层。据了解,每个准备脱钩的种子企业,都有一群副处以上行政级别的群体,行业人士形容他们是既享受着体制的“行政待遇”又领取着社会资源错配的“薪资”。“脱钩”是要动他们的奶酪,他们一定会一拖再拖,百般阻挠。
如何走:仍未迈出实质性脚步?
农业部种业事企脱钩的政策比较宏观,标准制定比较模糊,各个省份出台和落实的政策文件也很模糊,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在观望,在拖时间。有人形容说,很多地方的事企脱钩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尽管一些进行股权改革的企业,但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根本没有见到过公开招聘。
种业知名人士刘石认为,事企脱钩进展并不太顺利,到目前为止,事企脱钩还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里指的是体制内的企业真正分离走向市场化。因此,在刘石看来,还没有成功的例子。“但事企脱钩,体制改革是必须的。”刘石说。
林默染认为,确定为公益一类的农业科研单位,下设种子企业,参与商业性竞争本身就属于社会资源的错配,违反市场经济公平、公正性原则,现在所谓的“种业事企脱钩”也只不过是对以往错误政策的一种矫正。
那么,接下来的路该如何去走?
中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认为,一是事业单位改革与事企脱钩应一揽子解决。二是协调解决好不同部门政策矛盾的问题,三是切实解决好利益分享机制的问题。他还提到,国外种业模式可借鉴,但还是要摸索出一条切合我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种业企业发展模式,照搬的话至少现阶段可能会水土不服。
刘石表示,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子公司会针对不同地区筛选不同的品种和组合,他们在生产效率、管理效率、技术方案上保证品种适应性和稳产高产。国外种子企业要在育种方向、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上不断改变。
比如,育种家到企业后对产业的需求理解更准,向着效率育种转变,不只是高产,而是高效,考虑农民需求的品种越简单越好,生产过程中能够做到粗放管理,投入产出比,这就要求品种抗性好,相对高产。
“种业事企脱钩”虽迫在眼前,但不能流于形式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对企业产生实际上的积极意义,还不过是换了个方式“混吃等死”而已。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